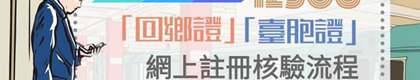16年來,這是張藝謀真正想拍的電影
電影、舞臺劇、體育綜藝、大型晚會,張藝謀的高產體現在多維的表現形式裡。無論臧否,他始終朝前走著。作為國內最受人關注的導演,真正屬於他的電影是哪一部?他如今的內生動力又從何而來?9月 30日,張藝謀最新電影《影》即將上映。連日來,該片的隨拍紀錄片《張藝謀和他的「影」》在不少城市進行了點映。不同于慣常的花絮,紀錄片把幕後所有的電影人作為重要角色。龐雜的人物構成,1400小時以上的總素材量濃縮剪輯成95分鐘的紀錄片點映,1000∶1的成片比,使得這部揭秘影片拍攝過程的紀錄片本身,有著豐富的讀解空間。它是《影》的部分劇透,也是《影》的誕生史,能部分揭示當下大陸電影劇組的生存狀況,也能部分詮釋 「張藝謀為何成了張藝謀」。
比如這一句——「我三四十年前看黑澤明《影子武士》的時候,就很喜歡替身的故事。」又比如這一句——「這應該是這些年我真正想拍的電影。」有人給「這些年」做了備註「16年」,即2002年張藝謀以一部《英雄》入世開始算起。
跳脫出帝王將相的範式,他把主角交給「不被看見」的那一個
《影》最早起意于朱蘇進的小說《三國·荊州》,但電影卻大大脫離了原作。因為張藝謀堅持,要把「影子」推到敘事的主位。
2014年,《歸來》還未完成,艾秋興把新劇本推薦給張藝謀,那便是《影》的雛形。「特別」,導演給出判定的同時,也提出一種設想:「我想把它徹底改一下,改成以替身為主的故事,而不是原來的重臣視角。」故事裡,沛國有都督名為子虞,既是武將也是謀士。因一次重創後元氣大傷形容枯槁,為避眼線,子虞讓外貌酷似自己的境州立於朝堂,而自己藏於斗室。從此,健碩、颯爽的境州替代了子虞的所有,甚至夫妻、生死……紀錄片裡,張藝謀對一人分飾兩角的鄧超說:「得讓境州出來,他是全片的靈魂人物。」
對於「古裝戲就是帝王將相、才子佳人」的慣性,張藝謀是有心想打破的,「我們古裝電影拍了一套又一套,但脫離慣性的並不多,我想用一個替身的故事來破一破」。戲裡,主角可被稱作「草根」「平民」;戲外,張藝謀同樣有心把「不被看見」的人推向前臺。
於是,紀錄片《張藝謀和他的「影」》更像「跟著張藝謀幹活是種什麼感覺」。此片中,武行、燈光師等觀眾略知一二的工種有之,選角導演、場景設計師、現場效果組這類鮮少被鏡頭關照的工作人員也有之,甚至跟了張藝謀20年的廚師、劇照師也都一一入鏡。還有個細節,每當子虞和境州同框時,與鄧超配戲的是演員封柏。從戲裡到戲外,這是個徹頭徹尾需要隱去自我的人。全片殺青前,張藝謀特意給了封柏一個角色,以他本來身份。
褪去色彩的一刻,那是張藝謀遁入了另一種極致的形式感
除了褪去子虞的主角光環,《影》還褪去了五光十色。絕大多數時候,黑白水墨調貫穿始終。前不久的威尼斯電影節首映後,「洗盡鉛華」被影評人反復使用。
為什麼要「素面朝天」?紀錄片興許從側面回答了「少即是多」。
比如影片裡看似顏色少,黑白灰三色足矣。但為了從水墨屏風的光影切換裡品出子虞之妻小艾的心境遷徙,臨時換布料、換漆工,捕捉自然光景與造物的互動,是導演在極簡的色彩中做的加法。比如片中戲份頗重的雨,「天落水」的背後無不是「人控」,如何根據不同的鏡頭、迥異的景別來造雨,雨線打到武器上該成多大的夾角,雨滴在怎樣的光線下才能噴灑到演員臉上又不至於讓人面目猙獰,看似最簡單的雨,同樣指向極致。紀錄片裡的種種第一人稱敘事,重塑了《影》的誕生,也提煉了張藝謀的部分導演關。
回到2002年以前,大陸電影市場化前夜。張藝謀徜徉的文學的殿堂,他鏡頭下的主人公,或極盡謙卑,臣服於命運;或放蕩浪漫,豁出人性底色,悲壯地掀起生命呐喊。他承認,自己是有些微焦慮的。北影82級學生裡,張藝謀是全校年齡最大的那個,「比起同學,我起步晚,急於表現出原創的精神來,就怕沒時間了,所以作品就呈現出極致的形式感的張揚」。從《英雄》開始,張藝謀不避諱面向票房、面向市場。大風起兮雲飛揚,他的故事開始躲在影像背後,由畫面的力度牽引情節的起伏。
近年來,關於大陸電影的種種爭論中,「第五代尚能飯否」幾乎成為常駐話題。尤其是2018年,在大陸影市順風順水的成了徐崢、寧浩、「開心麻花」他們。同叱吒風雲的新銳們相比,《影》或曰張藝謀的創作做派似乎姿勢老套、節奏遲緩。在此當口,《影》及其紀錄片同時上映,可能印證了北野武的話:「什麼是藝術的本質?是一種壓倒一切的任性吧,是一種純粹的浪費吧。」
本週五,等風來,《影》動。
[责任编辑:韩静]